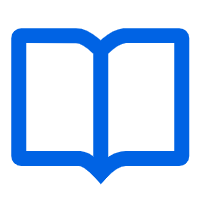爱尔兰有几家医学院?
我在1990年的6月间到了都柏林,在那里待了四个月,就是为了我能有机会旁听那里的医学院的讲课。我认识了一位医生,并和他很熟悉,他邀我到他家里吃饭。我很高兴能参加这家人的一次家庭晚宴。他们家在都柏林的中南部。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汤和肉),孩子们(6个男孩和3个女孩)在一旁玩耍的时候,主人问我想不想听听他们的家庭咒语,以让我的耳朵在吃晚饭的时候更能适应他们的语音。我说我很乐意听听。他就用食指在我耳边轻轻的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在我此后的一次访问中又重复了一次。这次访问是在1991年12月份,是在都柏林郡的沃特福德。我这次是和25位大学生在一起,这是一次医学院的公共医疗实习(它总是在学生离开学校前的最后几个月进行),这次访问的目的地是托尔里镇。当飞机在沃特福德降落的时候正好是黄昏,于是我们(9名女学生和16名男学生)就前往霍里迪伯恩宫,在那儿我们受到了宾至如归的欢迎。
我第二次去沃特福德是1995年,那时我已经有了3个月的妊娠反应。我听说,在霍里迪伯恩宫有一个专门为孕妇提供的健身房,在离开的前一天,我就和一位护士预约好,以确定第二天早晨在那里碰面的时间。我早晨很早醒来,就急忙去淋浴(那儿的温度可控)并做早晨的训练,但是在练习仰卧起坐的时候,我感到头晕,并且出了很多汗。我很难去解释我当时所感到的虚弱。我回到健身房休息,并喝了一杯牛奶。在我训练结束之后,一些护士来看望我。她们都很年轻,我猜想她们都是刚从医学院毕业。当我提出想谈谈的时候,她们都很乐意跟我谈。一位护士告诉我说:在分娩之前,婴儿可以通过脐带从母亲的血液中得到那些为他的肌体构造提供必要的成分。然后,当他的身体发育到适当的时候,就会从胎盘进入他的母亲的身体。那时,他就中断了和母亲的血液循环,因为婴儿有了自己的心肺(胎盘和脐带)来为他的体表提供血液。在我听了这位护士讲的各种情况之后,我感谢她给了我知识。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参观了沃特福德郡的许多地方。在我所访问的每一个公共场合,人们都很高兴见到我。这令我想起1966年的一次访美。在费城,一个小孩儿(大约5岁)问他的母亲是谁。他母亲解释说:“这个女人是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一个朋友。”于是,那个小孩儿就过来握住我的手并说:“我希望你的朋友能成为你的儿子。”我无法准确的解释我当时的感觉,但是我感到了一种深刻的尊重。甚至那些只是偶然听见我谈话的人也似乎都被我的话题所吸引。人们很乐于告诉我他们的故事,尽管我还不是很熟练的掌握这种语言(英语),我知道如何抓住听者乐意交谈的欲望。就像1971年在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的国家图书馆召开的一次国际生物物理会议上一样,人们很乐意听我说话。(那时,我就对科学家们的各种不同工作极其感兴趣,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当我回到法国时我就着手翻译那些笔记。但是,那毕竟还是太专业了。)
然而,在当今,在某种程度上,我怀疑医学和牙科学专业人士会拒绝理会一个非专业人士所发表的意见。当然,这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一旦公众开始不相信医学,医学便将会失去它作为一种公正职业的地位。然而,公众的这种缺乏信任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充斥着广告的社会,很难排除人们以歪曲真相的方式来争取利润。在这种状况下,公众的怀疑便是自然的了。但是,医学专家无法肯定他们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工作是否得到了公众的信任。我的意思并不是指由患者组成的人力集团,而是整个社会。因为社会将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医学权威发出警告:它已经开始怀疑医学权威了。
对一种新疾病的发现总是要花费一段时间的。正是通过这种滞后,这种新疾病在医学界才有机会被认识,并得到恰当的命名。于是,那些先于这种发现的人便变得似乎是“妄自尊大”了。在我看来,“妄自尊大”这个词并没有充分的表达那些宣称已经发现一种新疾病的人的矛盾心理。这里所说的“新”绝不是指那些以人类作为受试对象并经过精心设计的实验所发现的疾病。在历史上,那些宣称发现新疾病的人将得到那些把新知识整合进去的人的工作成果。下面我描述的事件就是这种相互关系的一个例子。
例如,我在1990年6月访问爱尔兰时所发生的事件。我已经了解到:都柏林的医学专家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致命疾病,它的症状是在肺部制造大范围的炎症。这种病以非特异性的方式开始,患者发烧,并有严重的呼吸问题。正如这种疾病所造成的影响,和它的病原体尚未为人所知一样,这种疾病在那时还没有名字。我在爱沙尼亚一位朋友的姐姐,那位医生,已经感染了这种疾病。这位朋友曾告诉我,他已经将这种疾病告诉了他的同事们,但是“他们说他已经得了肺结核”。但我知道,肺结核患者是无痰咳嗽的,而这位爱沙尼亚的医生却不断地咳嗽。在我从都柏林回来之后大约一个月,我听广播说这种新的致命疾病是以一位微生物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就是“霍乱微生物”。
现在,我想告诉你们我看到的关于新疾病的发现的故事。都柏林大学的前身是都柏林医学专科学校,在19世纪中期,这里主要培训医学院的学生和药剂师。现在当我想起这儿的时候,我想到的则是学校的主楼,1813年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它似乎比所剩下的古老建筑要新得多。我已经在都柏林待了大约五个小时了,已经参观了国王大学医院,那里就是著名的心脏移植手术的所在地。这个肝脏移植的手术是为了使一位患肝萎缩的4岁大的女孩继续生存而做的。我现在正要从一个非专业人员的角度来观察大学。
我走在大街上,在主楼前。两个学医的年轻女子正在聊天。她们是医学生。我已经注意到了她们,因为她们所穿的白大褂在灰暗的色调中分外显眼。一个护士向我解释道:“当一名护士是非常困难的:你必须非常强硬,冷静,并且总是在你的脑袋里不断地进行计算。你必须迅速地判断哪一边的伤口是坏的,需要多深的缝合,什么的。”这使我想起,在我参观宾夕法尼亚大学牙科大学的时候,那里的一位教授已经解释过:“当一名外科医生是很容易的,但当一名牙科医生则比一头驴子还要辛苦”。在后来的一次访问里,当一位护士告诉我有一个学生已经学习了3年之后由于考试不及格被迫退学时,我感叹:“医学教育如此之难应该让所有的人都害怕"。但是,在主楼前面,学医的女孩子们只是在聊天。
当我在都柏林大学医学院的校园里漫步时,很多男孩子们看上去非常忧伤。这肯定让那些正在寻找职业的男人感到担心。当然,他们在这种新疾病发生的时间要离开医院是太高兴了。而女人们却面带微笑。他们也许都在想,和这些人一起在医院工作太紧张了。虽然,这种新疾病叫“肺炎”,在都柏林的医院里,病人们却只是“受到感染”而没有“患肺炎”。在门厅里有像医院一样的装备:桌子,医用架,输液,一些药物和用来消毒的消毒剂。当然,没有病人。这儿不过是医学院学生的实习场所。这些孩子看起来和我的孩子们一样大。
我在这里与学生们交谈,他们告诉我,疾病是以一种非常可怕的新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新疾病的影响非常严重,因为除了肺部的炎症,它同时还引起发烧,低血压和少汗。而最重要的,这种疾病甚至还在人体内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就可以传播。没有症状,也就是说,当病毒还在人体的皮肤上的时候便可以传染给别人。于是,从某个被感染的人身上经过空气飞沫传播出去的病毒可以在四到七十二小时之内引起疾病。这解释了为什么新疾病的疫情爆发如此迅速的原因。它甚至比流感还要严重,因为对于流感来说,“潜伏”期要长很多(在12到24小时之内)。
这些学生还说,这种新疾病可以影响任何年龄的人(从6岁到70岁),并且,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肺部,这可以从它的死亡率高达90%上看出(只有不到10%的患者可以幸存下来,而这一部分特殊患者都受到了器官衰竭的困扰,他们的身体各个系统都受到了影响)。他们的谈话被一个护士打断了。她正忙着整理教学资料。她对学生们说:“你们必须小心。由于肺炎双球菌在70年代早期已经是一种很严重的威胁了。必须记住,它的死亡率仍然很高”。我不明白护士的话是什么意思。当然,肺炎双球菌是一种古老的病菌,它“很危险”。这种疾病爆发于1916年,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造成了近100000个美国人的生命丧生。但是,对于新疾病来说,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
学生们建议,为了使这种新疾病免遭人们的遗忘,我们应该为它举行一次特别的纪念活动以抚慰死于这种疾病的人们。为了纪念它,学生们计划组建一个俱乐部。这种新疾病的发作应该被作为一个警告,以让人们注意那种新的致命的病原体会带给人们怎样的威胁。